《消失中的江城》这本书其实我是第三次读阅读,第一次是在网络上,忘记在那个网站或是博客看到该书的译文,阅读了本书的前几篇,那种平淡的文字:“坐慢船,由重庆顺流而下,我来到了涪陵。这是一个温暖,清爽的夜晚,在1996年八月的尾声。”,此后何伟(彼得·海斯勒)在涪陵这个地方的师范学院当了两年的支教。而开始的几篇就是何伟刚到涪陵前几周的所见所闻,我还以为这些只是几篇散文而已,没有追读下去。
第二次阅读是几年前,不知道为何那时候该书只有第一部。当读完第一部时心里总是有所牵挂,后来呢?后来呢?但是没有下文。而第三次阅读是在”方所”中发现他的《寻路中国》后回过头来重温阅读他的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《消失中的江城》是才发现原来自已以前阅读的只是一部份而已,于是当我阅读完《寻路中国》后在Kindle上花了几天把《消失中的江城》读完。
我没有去过重庆,也没有去过涪陵。对于重庆的了解只限于电影《日照重庆》、《三峡好人》、《狂疯的石头》和平时所吃的麻辣烫,而对于涪陵的了解,真的仅限于像何伟所说的“涪陵榨菜”。但在《消失中的江城》中我了解的不单有“涪陵榨菜”,还有那里的乡土人情及人对生活的那种平淡与悲伤,乐观与坚强及食品的火辣辣。该书平缓述说那种日子,记录着那段平淡的生活:“跑步,教学,吃饭,下乡,踏青,所遇”等等。但在述说这些平淡生活的同时,体现出日子的不平淡。我不懂得如何去与大家分享这本书,但我喜欢何伟这种平淡的述说及书写。这才是平淡的生活,不平淡的日子以下是网络上的一篇书评:
《江城》:模糊的脸,清晰的中国
《江城》中,何伟写到的最后一场冲突发生在他离开涪陵之前。他和同事亚当想拍一些片子,作为他们曾经在这个小城生活过见证。他们想拍下一切关于涪陵的记忆,他们走过的街道,生活过的校园,交往的学生,结交的朋友,还有那些依然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。何伟原本以为,普通人很难拍,只是因为他们发现你正在拍摄,就会放下手头的正在做的事情,充满好奇地围观和追问。他没有想到还有另外一种“好奇”,一种XX敏感性的“好奇”。在拍摄的间隙,一个自称“市民”的人很突兀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,呵斥他“禁止拍摄”,“这是违法的”。
这次冲突发生的缘由不是因为这位“市民”的敏感性,把他们误读为记者,而是因为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X观。X民也好,乌合之众也好,一旦成为了某种隐秘XX的诱因,很容易陷入失控的边缘。何伟说到了他匆匆逃离暴民的围观时的一个印象,“我所能见得的只是一群模糊的脸”。还有他从这次拍摄中领悟出的经验:“它所展示的,只是直白的,关于涪陵生活的无用的真相:在两年后,我们依然是外国人,即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中,也在人们看我们的方式中。”
最让人感觉到悲哀的莫过于此。他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两年,极力融入当地的生活语境,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当地人,说着蹩脚的中文,吃着抄手,呼吸着污浊的空气,奔跑在崎岖湿漉漉的山道上。但最终的真相还是“我们依然是外国人”。
1996年8月,彼得·海斯勒和他的同事亚当·梅勒以美中友好志愿者的身份来到重庆附近的小城涪陵教书两年。那一年他27岁,牛津大学的毕业生。他之前从未听过涪陵,涪陵在这之前五十多年没有见过外国人,他们互不相闻,却千里相会,他还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何伟。两年之后的1998年的冬天,当他回到美国的家中,花了四个月时间,从远方观望和书写这个城市的时候,一切的记忆都开始变得清晰起来:那长江上的点点星光,小城噪杂的声音,污浊的空气,挑着扁担的棒棒大军,围观他们的群众,都变成了一幅幅画面。
这个城市最初留给他的印象如此丑陋:高亢,忙碌,拥挤,脏乱;交通是一团糟,行人们互相推撞;商店总是冗员,摆满商品,街上到处挂着宣传标语;没有信号灯;司机们一刻不停揿着喇叭;电视机的屏幕在狂闪,人们讨价还价;沿着主街有一排模样可怕的树,灰色叶子上布满了煤灰,整个城市都覆盖着煤灰。“这城市和它生长的土地截然不同,除了那一小片旧城区外,这里没有一点历史的痕迹。旅行穿越四川的乡村是去感受它的历史,多年来人们的劳作给土地塑了形,那许多世纪以来厚积于其中的人类的重量。但四川的城市们总是没有时间感。它们看上去太脏了,不可能是新的,又太丑,如制服般雷同,是以不可能是旧的。”
他在涪陵师专教授莎士比亚和文学,不得不与陈旧的观念做迂回的斗争,用文学的诗意调动学生的心灵去感受文学的美好,而不是XX的套路,整齐划一的僵化思维。他开始意识到,伟大文学作品的部分力量,来自于它的世界性,它的普世价值:一个四川农民的女儿能读到贝奥武夫,将之与她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,一班的中国学生能够倾听莎士比亚的诗歌,而看到一个无瑕的汉朝美人,“但与这种力量相随的是脆弱,因为总有人想要借伟大作家的力量为自己所利用。”这是隐晦的说教,迂回的批评,善意的提醒。
一个外国人,不远万里来到中国,在这里生活了十年,写了三部关于中国的著作,颇受中国读者的追捧。我们的好奇不免集中在:他笔下的中国是什么样的?我们又为何对他笔下的中国产生兴趣?《江城》里的涪陵是中国城镇生活的一个真实缩影。何伟在刚到涪陵时,说到了一个强烈的、无时无刻不处在被围观状态的印象,“我所见的第一样物事,乃是我自己和亚当。这有点吓人,因为在我人生中从未被人如此密切观察过,一举一动都被复述,被评估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被谈论,被记录。”这种怪异的经验,也是我们阅读《江城》的经验。我们从一个外国人眼中看到了自己的一切都被描慕出来。这种吊诡之处在于,我们从别人的眼中看到的那一幕幕再熟悉不过的场景,其实是被陌生化的。何伟写出了他的异质经验,我们阅读的时候产生了陌生感。这种陌生不是因为真的不熟悉,而是因为距离——距离不仅仅能产生美,还能引发我们对这种熟悉事物陌生的沉思。
以何伟在涪陵时对“个人”这种观念的观察为例。他说在涪陵住的时间越长,就越是对“个人”这一概念的看法所惊讶。在涪陵的人们,他们自我的意识都是格局别人对你的看法所定义的,“那总是儒教的目标,定义个人的位置,乃是严格按照她与别人的关系来进行:她是某人的女儿,另一个人的妻子,又另一个人的母亲;而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责任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社会和谐的方式,然而,一旦和谐与打破了,缺乏自我定义这一点,会使得重建变得困难。”
也正是这种对外在价值的投射定位,使我们很少能做到独立思考。出现问题时,我们的第一反应不是积极应对,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,权衡利弊,反而丧失了最佳解决问题的时机。我们习惯于集体和社会这样的宏大概念,反而忽略自我价值的清晰定位。这个国家对牺牲精神的过度阐释和宣传,对志愿者精神的误读背后,都是这种“个人”概念的歪曲所致。
何伟在《江城》中还提到了这种异质经验的例证,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他的中文随着教学的深入,已经能与学生们正常交流的。随着他在课堂外与学生的交流更频繁,他发现每当有XX话题时,他们就习惯用中文。这让他十分惊讶,因为英语本可作为他们的秘密工具——在校园外,几乎没人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,用它来讨论上述话题是最安全的,不怕有人听到。但终于,他意识到,他们在敏感话题上说中文其实源于一种恐惧,这种惧意来自长期压抑的生活语境,XX审查,思想X脑:“但我也察觉到,真正的惧意,他们真正怕的,是他们自己:几乎所有的限制,都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头脑意识中(自我审查)。”
何伟通过《江城》提供给了我们一种观察自我的方式,即通过一种异质经验的阅读完成自我的审视和反省;通过一种对熟悉生活的重新叙述察觉出其中的文化冲突——不是缘于中西方文明的差异,而是觉醒的个体与模糊的群体像之间日益分明的冲突。
作者:思郁
2012-3-24书
由于敏感字原因,有些用XX替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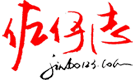
好久好久没有静下来好好看本好书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