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一本值得去阅读的近代史读本,也是我第一本在亚马逊中国购买的Kindle读本,只需要1元。它源于自人民大学的一门热门选修课,即张鸣老师开设的政治史公开课,它靠同学们口碑相传而走红校园,最终使更多的人对这段看起来枯燥无比的历史重新认真审视起来。读完这本书,你会发现,原来我们以前读的历史原来是这么的不真实,我们以前所了解的历史真相竟是这样,有点惊呀与烦恼。
这门课为什么如此受欢迎?原来在张鸣老师的还原下,中国近代史变得如此复杂、精彩,又是如此的颠覆,它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,绝非教科书上的忠奸两列、黑白分明。当诸多人物与史实呈现在我们面前时,难以用一句简单的是非作判定,在正视一段被扭曲的中国近代史的同时,我们也能发现国人今日问题的精神根源。以下是它的第一讲:第一讲 中国近代政治史开场白。
全文如下:
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?我的一个朋友曾提过一个很好的比喻:一天早上你起来突然失忆了,忘记自己是谁了,想想看你今后该怎么生活——你谁都不认识,这意味着忘掉了自己的历史。历史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,但实际上我们是离不开它的。其实对于一个民族,无论是其整体还是个人,记忆都是不可或缺的,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。很多人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失忆状态,所以一直安放不好自己的位置,在历史长河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,在世界格局中也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。
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课,大学本科都在开,但是名义上讲的是历史,实际上却不是当成历史课开的,而是按政治课开的,即使在历史系也是如此。这种课的主要目的是想给大家灌输一种世界观,一种意识形态,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观念史。所谓史实,是被要求服从某种观念的。如果我们今天从一个常人的是非和真伪角度来看,这样的历史就是伪史。上这种政治课的时候,大家都兴趣不大,经常睡觉或者看小说。但别看上课的时候不以为然,其实你还是或多或少会受它影响,一到在网上谈某些事情的时候,只要涉及历史,就不知不觉地把这套东西搬出来了。也就是说,我们会鄙视一个假的东西,但是我们依然依赖这个假的东西。这就令人很困惑。
我国的近代史,有一个范文澜、胡绳的基本模式。这种模式通常有两条线索,其中一条是帝国主义侵略论——自鸦片战争以来,西方列强总是侵略、欺负中国。强调这样一条脉络,由此证明我们这个民族是苦难深重的,同时说明我们的落后是因为别人侵略、欺负我们造成的。另一条线索就是革命线索——三大革命高潮,从太平天国、义和团然后到辛亥革命,总之就是一个反抗、革命的过程。这样一段悲惨的近代史,一段总是折腾的历史,很容易使我们忽略从晚清以来这么多丰富的变化,不知道该怎么走后面的路,不知道为什么要改革、要开放,为什么还要学洋人那一套东西。
事实上,如果我们不知道近代中国是怎样融入世界的,或者完全无视这个过程,而只强调我们一直在革命,那么我们就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放下革命搞建设,不会明白为什么要重新开放。结果也就只能是我们重来,再重来,重新开始鼓噪革命,重新开始鼓噪排外。可是这样一来,我们会回到哪儿去呢?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,面临着这样的困惑。
一、对于近代史的“三妇”心态
以往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有三种惯常的态度。在此,请允许我打个不严谨的比方。第一种是怨妇心态,凡事以哭闹为主,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,你们从头到尾都欺负我们,我们冤得要死,我们苦大仇深,比窦娥还冤。总是在哭,总是在闹。不仅哭闹,还时不时要掀起衣襟给人看:我这伤疤就是当初你弄的。
圆明园那几个水龙头能卖出天价来,就是因为这种心态在作怪。那几个水龙头怎么可能是英法联军抢走的呢?当时圆明园珍宝如山,英法联军会抢这几个按照西方的模式做出来的喷头吗?它们十有八九是在这个园子废了以后,被中国人弄到外边卖掉的。卖出去也就是当个摆设,当时仨瓜不值俩枣,现在却卖给华人,卖到几千万,可见国人这种怨妇心态已经根深蒂固。
第二种是泼妇心态,凡事讲打,打不过我挠。我要反抗,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,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,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,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,还挠不到脸上。但是我们觉得很好,还很推崇,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。如果当时斗争真有这么波澜壮阔,那英国人根本进不来,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有这段被称为半殖民地的历史。
第三种是情妇心态。它跟前面两种心态正相反,在它看来,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,不殖民我们怎么进步?但是被殖民的过程实际上是很屈辱的,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,尤其对这个民族的上层精英来说。如果这些上层精英曾受过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,他们就会感到更悲哀。但是情妇心态把这一层抹掉了——就觉得殖民是好事,能看到它给被殖民国家带来文明,却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夺和奴役。这种心态,其实有点变态。
“三妇”心态实际是我们国人对待近代历史比较常见的心态。有人说,这好像都不大对头啊,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历史和外来者呢?我说,我们能不能别在历史和外国人面前当妇人。你可以将其当做朋友,也可以视为敌人,只要自己别像妇人一样就成。关于心态问题,我觉得是在看待近代史的时候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二、中西两种体系
所谓近代史,如果按中国传统史学来说,就是晚清史。中国传统史学,是朝代史,唐史、宋史、明史、清史这样的。如果按世界史的划分来说,晚清史只能算是中国近代史。我们怎么看待近代史,或者说怎么看待我们的晚清史,这个历史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,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。在我看来,晚清历史的本质就是西方把中国拖入它们的世界体系的过程。西方有个世界体系,我们有一个天下体系,或者叫朝贡体系。但是我们这个天下体系(朝贡体系)是内敛的,是内缩的。就是说,并不是我去打了天下,征服了某块殖民地,然后建立起一个朝贡体系让其他人来服从我,而基本上是用一种文化的、一种以德服人的方式让周边国家来仰慕我的文化,然后向我进贡;或者以大国之威,让周边国家向我朝贡。有的朝代也会打一下,占了地方,不是当殖民地,而是直接占领。但往往控制不住,朝代末期又退了出来。在这个天下体系里,我呢,是中心,但并不知道世界周边有多远。朝贡体系就像一个圆,这个圆的中心是中国,而外延有多大不知道,多大都可以。你来不来我不管:你来朝贡,那是你向慕王化;如果你不来呢,随你的便。显然,这样一个体系不是向外输出的体系。但是西方自十八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后呢,实际便形成了一个输出型的体系。它不断地把这个体系向外输出,把它所遇到的,能殖民的就殖民,不能殖民的也要把其纳入自己的体系中来。在这两种体系的碰撞中,我们的天下体系显然崩溃了。
我们干不过人家,就得听人家的。中国人开始是被动接受,人家兵临城下,我们捏着鼻子忍受;后来有点主动性了,逐渐产生了解人家的欲望,开始学习《万国公法》。我们在1860 年开始设置同文馆的时候,主要学习的就是《万国公法》。我们开始想了解这个世界体系是怎么回事——所谓的《万国公法》,其实就是西方那个世界体系的规则。
开放口岸也是如此:开始是人家逼着我们开放,这次开放一些,下次再开放一些,后来我们就自己主动开放了。学习亦是如此:开始是被动学习,然后是半推半就、中体西用,最后是全面地学习。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是全面地学习。不光是西学东渐,而且是西俗东渐。如果注意看一下那个时候的报纸,就会发现当时所有西洋的东西都被冠以“文明”两个字。西式礼帽是文明帽,手杖是文明棍,自行车是文明车,连火柴都是文明火。话剧是文明戏,我们的京剧叫旧戏。凡是西洋的东西都意味着文明,都意味着是需要我们学习的。这说明什么呢?说明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心悦诚服地被拖入了这个体系——我们认账了。为何会这样?因为西方世界迎合了人类创造和追求财富的需求,一旦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普及开来,会产生一种内在的驱动力驱使人们去进入它们的世界。这就是一个近代史的过程。
可能在我们今天看来,西方的世界体系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。它是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建立的,跟工业革命息息相关。如果按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说法,其实西方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偶然,但是这个偶然却造出了大事。为什么呢?因为工业革命创造出一个新工商文明,而现代工商文明这样一个潘多拉之匣被打开后,世界就变了。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,或早或晚都得跟着走。
我觉得这个文明可能是不好的,它对资源掠夺和榨取得太厉害,对环境破坏得太快。就像《庄子》里那个故事,说是一个老头在浇园子,园里有一口浅井,老头每天拿个瓦罐跳到井里,打一罐水然后爬上来浇。子贡问他为什么不弄个桔槔(就是杠杆),那样多方便。老人说他知道那个东西,但是他不用。为什么要用那玩意儿呢?它是机械,人用了机械就起机心了,就想着怎么取巧,从此天下就不得安宁了。其实道理就是如此,一旦把这个大工业文明唤出来之后,人们就天天想着怎么取巧——我们去发明创造,翻着花样地想着怎样去榨取资源——人类几万年的历史都没有弄出这么些事来,但这几百年就都实现了,而且后面会怎么样,人类还不知道。但是世界一旦进入这个轨道,潘多拉匣子一旦打开后,就回不去了。你想进去也罢,不想进也罢,都回不去了。你看这世界哪个地方还没有进入这个体系?哪个地方还没有受到工业文明的污染?哪个地方还是桃花源?没有办法。你只能在这个文明的基础之上,想一点补救的办法。比如出现了土壤板结、农药污染问题,我们只能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想办法发明一种污染较小的农药,以及使土地板结程度较低的化肥。我们只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往前走,不可能回去了。人类都不可能逃脱这个被工业化的命运,抗拒它是没有用的。西方的发展道路或西方的世界给我们带来这个东西,世界的命运已定,已然逃不过去了。
三、中国的抵抗
所谓中国的反抗史就是抗拒史,其中抗拒最激烈的就是义和团,他们把西方的一切都排斥掉了,把所有沾洋边儿的东西全部干掉。从街上抓来一个长得像学生的人,搜搜包,如果发现里面有一张洋纸,那么那个人的脑袋就没了。有一支铅笔也不行,钢笔更不行。当时他们盲目排外,排斥一切。而这样做换来的是一个很悲惨的结果,我们被迫签订了《辛丑条约》。根据条约规定,外国可以在中国北京驻军,从山海关到天津一线,中国军队不能驻军,外国军队却可以。天津也是如此。后来中国人要在这一带驻军,只能把军队服装换成警服,以警察部队的名义进驻。不仅如此,中国还赔了人家四亿五千万两白银。
这种抵抗是无效的,不仅中国的抵抗无效,其他地方,诸如奥斯曼帝国和非洲祖鲁人的抵抗也是无效的。任何地方的这种抵抗都是无效的,因为这是大势所趋。潘多拉的匣子一旦被打开,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了。在西方的工业文明没有出来之前,我们可能有很多种选择。比如,我们可能还在慢慢地走,出门还骑驴。进京赶考的人给老婆写封信,估计她三个月以后才能收到。过去的风俗,长久以来都这样,或许现在某些地方还是这样。因为中国两千多年大体进步不大,拿秦朝和清朝比的话,我们的进步有限,尤其是技术进步有限。有人可能说,秦朝烧不出瓷器来,清朝可以烧出许多花样的瓷器来。但秦朝的陶罐子也能顶用,一样可以煮饭、打水。还有马车,秦始皇那个时代的马车,跟现在我们看到的马车没什么本质区别,除了现在的马车是胶皮轮子而已,进步非常有限。
那个时候好不好呢?女性可能差点,只能待在家里,不能出去上学,婚姻大事都由别人做主,看上谁也不能直接嫁给他,除非你是卓文君。男性可能感觉还好,如果有本事就出来,考个秀才、中个举人很爽的。很多人觉得我们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些东西。现在人们普遍活得比较紧张,文明越往后发展,人们越紧张,也就没有闲暇去想其他的。一些有钱的读书人闲下来,就会想现在的生活太没意思、太乏味了,过去的日子多好啊,田园诗一样的生活。吟吟诗,喝喝酒,谈谈风月,一天到晚没什么紧张事,一觉睡到自然醒,多舒服啊。人们会怀念这样的生活。
实际上我们人类很难,作为人,很难有一种状态是感觉非常好的。当我们回头看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,既然我们不可能逃脱这个命运,那么我们的感慨,我们的愤慨,或者我们的不满意都只能是一种牢骚而已。那么我们干吗要这么折腾呢?这样想来,心情就会好一点,就会平和。我们可以设想,有没有可能摆脱这条道路?其实历史上很多人都在思考,是不是可以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。这个想法不是今天才有的,中国人一直都想走一条特色道路,一直都在想。
我们最早学日本。看上西方直接学西方就行了,干吗学日本呢?日本纳入西方是后来的事情,当时还不算西方呢。我们之所以学日本,是因为觉得日本好,学日本是捷径。我们认为日本学西方是学了一条捷径,我们如果直接学捷径就更捷径了。什么叫捷径呢?就是抄小路。人家这么走,我们抄小路,抄近道,赶上去,走到前面去。后来我们又学俄国了,也是想抄近路。学俄国实际上也是学西方,看上去俄国人抄小路突然之间就富强了,就厉害了,就变成苏联可以跟美国人抗衡了。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想学美国,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了临时政府,那就是美国模式。为什么学美国呢?因为当时我们认为美国是最先进的,我们把最先进的直接拿来用就行了。
抄近路学人家,是想把那些貌似是捷径的东西学过来,这本质上就是想走一条中国自己的特色道路。这条道路无论怎样,还是离不开工业文明。也就是说,无论怎么讲中国特色,都不能回到孔子时代老牛破车的道路上去,都不能回避工业文明自搞一套。沙特是一个神权国家,但是它也接受西方文明。有时候接受得比较过分,一些大阿訇们会生气抗议。国王一看大阿訇们抗议了,就悄悄令手下把大阿訇坐的高级轿车全部收走,封上封条。大阿訇们出来一看车被收了,就问为什么。得到的回答是:你们反对西方工业文明,而汽车那些玩意就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,所以你们不能坐。大阿訇们想,不坐高级轿车,靠腿走路太难受了。于是之后再开会时,就同意了一些条例。也就是说,即使今天再保守的人,有一个问题也是能够想通的:他绝对会享受西方文明的成果,有小车就不坐大车,有电梯绝对不会爬楼梯,如果爬一定是为了减肥。
我们现在能不能摸索出一条全新的路?我觉得很不容易,因为我们很难走出这个大框架,很难走出来一条跟这完全不一样的道路。走自己的路,说说容易,做起来难。
还有,中国人能不能不挨打?毛爷爷说了,中国人学西方,但是为什么先生老打学生?的确,他们老打我们。但是回过头来看,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如果不挨打,能去向西方学习吗?说实在话,我们走到今天也可以说是被打出来的。不挨打就学西方,日本人做到了。佩里舰队去了,一看日本人没什么大船,就递上条约订城下之盟,日本琢磨琢磨就软了,就同意开放——日本的开放不是从明治维新时开始的,而是从幕府时代就开放了。还没打,日本就开放了,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学。但是中国人做不到,这可能跟国民性或民族性有关。不挨打,就很难学人家,被打得很惨,才学得好一点。比如,在1901 年之后,那次被打得最惨,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从皇宫里逃了。大热天的,太后那么大岁数了,化装成农妇,坐着骡车,一路风餐露宿,还穿越苞米地,一身痱子,两天两夜连水都喝不上一口——这下可受苦了。所以我说帝王之尊得挨点饿,挨过饿后,施政、做事什么的就好一点。总这么养尊处优的话,根本没法进步。
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发现,日本的传统其实维护得很好,西方看东方很多方面是看日本。日本的历史和古代文化都不如我们悠久,但是为什么它在西方受到的评价那么高?就是因为它走出来了,它成功了。你现在成功了,人家才会重视你的过去。如果你现在什么也不是,那么你的过去就是一堆垃圾。就是你想发扬国粹、弘扬传统,都没机会。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对待历史,不能走出历史,那么我们过去的历史就什么都不是。
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这段历史,又该怎么去做?很显然,我们需要冷静地审视过去,不能再当怨妇、泼妇、情妇。冷静地审视过去,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,尽早学得聪明些,不要总在一个坑里反复折腾、反复跌倒。如果我们不能很正确地看待这段历史,就很难吸取教训,很难避免过去的悲剧。我们必须从心理上走出我们的中世纪,才有前途,过去的辉煌历史才有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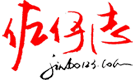
一直觉得张鸣写的历史书很棒。
我反而是第一次知道张鸣老师,也是第一次知道历史可以这样讲,以往学历史是只是听故事,而且听的是一面倒的故事。
不谈书,人大最近因为女神比较火啊。。。